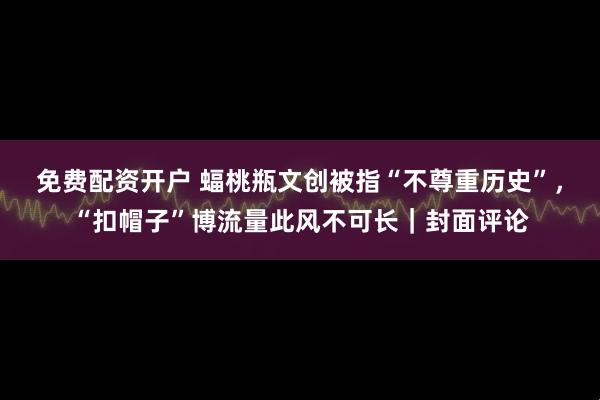

□蒋璟璟
日前,有网友表示,自己在上博东馆购买的以上博馆藏文物“蝠桃瓶”为灵感设计的冰箱贴文创具有“发光功能”与“瓶底开孔”设计,令人联想起该文物流落海外期间被改造为灯座的遭遇,涉嫌“不尊重历史”。7月9日上海博物馆馆方介绍,瓷瓶台灯已在上博文创商店销售近三十年。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,上海博物馆始终尊重历史,了解文物特质,并征询了捐赠人的意见。(澎湃新闻)
历史,是既定的、客观的,而历史叙事却往往难以摆脱选择性呈现与主观演绎的影子。最近,一件蝠桃瓶的身世,就陷入了某种“各自表述”的舆论风波中。有网友宣称,上博一款冰箱贴的“发光功能”与“瓶底开孔”设计,与蝠桃瓶流落海外期间被填埋沙泥、改装为灯座的特殊经历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呼应……其言外之意,无非是想说,这一文创产品是“忘记屈辱,消费苦难”、是“对历史的健忘,对情感的挑衅”。如是这般,小小的冰箱贴,被扣上了重重的帽子。
的确,这件蝠桃瓶作为回流瓷器,其身世很是颠沛,但并不那么凄惨。根据业界说法,其在海外藏家手里珍藏多年,“保存状况非常完好,几乎没有什么损伤。”至于说其曾被改造为台灯,也属于是特定社会文化下的常见操作,这关乎器物观、审美观,而并不涉及故意的矮化与羞辱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,一个寻常的中外文化交往案例而已,实在没必要苦大仇深渲染悲情,更不该为博眼球强说“仇”。
任何“瓷器”,最初都是作为商品、工艺品而存在的,而在时光的沉淀中,其中的一部分成了文物。“文物”很珍贵,这是基于其工艺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研究价值、历史价值而言的。这里面,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“历史价值”,其不仅是够老够久而已,也包括了它所经历的那些事情、所承载的那些记忆。以这件“蝠桃瓶”为例,其所牵出的瓷器贸易轨迹、文化生活课题等等,都是其内在“历史价值”的一部分。这是必须正视的,而非想当然地归为“苦难史”遮掩回避。
“文物苦难史”,更多的是关于毁损、掠夺和失佚的具体悲剧,而不应该用拟人化的情感,来将之扩充为一个泛化的概念!守护文物,绝不是将之“人格化”乃至“神格化”,对一件瓷瓶搞“为尊者讳”的那套,未免加戏。关于这件蝠桃瓶,一些人故意把它的身世说得那么不堪,这难道不是伤害力更大的羞辱吗?讲述文物故事,若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,而误入撩拨情绪、煽动仇恨的小作文流量赛道,这才是真的“不尊重历史”。
周边文创产品开发,是文物的活化与延伸。作为文物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免费配资开户,客观事实、专业判断,始终应该是先决性的。不被谬误所影响,才能离纯粹的文物世界更近。
嘉喜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